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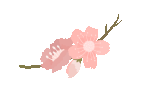
黄昏下的河边村最是好景致,一轮橙红的圆日衬着火烧般的晚霞云彩,在小河边边上映照出一副堪比最好画师绘成的落日余韵图。
齐妈妈坐在小河边的一块平坦石头上,手里搓着一盆衣裳,跟她在一起的还有几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妇人,个个垂着头,不说话,只是手上活计不肯停下来,周围皆是衣裳布料摩擦出来的“哗哗”的声音。 “齐大嫂子,你家大小子怎么样了?”过了一会儿,跟齐妈妈挨得最近的妇人忽然打开了话头,她看了看两边,压低了声音,问道:“腿上的伤不能拖着呀,万一落下病根怎么办?” 她满脸担心,用胳膊肘戳着齐妈妈。 “唉……”齐妈妈听到她问,眼角的皱纹缩成一团,愁眉苦脸地摇摇头,说还是那个样子,骨头断了,加上没能送医,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,前些天她男人去山上挖了点活血化瘀的草药,先将就着吧。 妇人也跟着叹气,齐家的大小子是个有出息的年轻人,身强力壮还念过书,她家里有个年岁合适的姑娘,原本是打算说亲事的,可是冷不丁地碰上这一茬,妇人便琢磨着,还是再等上两年再说吧! “要不……”妇人神神秘秘地张望了两下子,几乎是趴在齐妈妈耳朵边上去了,道:“你去找找邵家年轻人吧,我听说那两兄妹有本事的。” 齐妈妈摇摇头,她先前就说要找的,可是她男人不同意,说一个二十岁的年轻小伙子带着个残疾丫头,怎么看都像是谣传的话,这种事情不好乱找人。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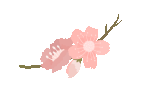
两个人正在悄悄咬耳朵说话,却见个七八岁的小小子着火似的奔到河边来,对着几个洗衣服喊道:“娘,娘,有个车子来了,要抓邵哥哥和七儿姐姐!” 小小子喊得起劲,几个洗衣裳的都听到了,赶忙站起来,三两下擦干净了手跟着小小子过去看,然而等她们赶到的时候,只看到一辆黑漆漆的小汽车屁股喷着烟,轰隆隆地朝着村子外去了。 “吓死人了,”小小子指着车尾巴影儿说道,“来的人气势汹汹的,穿着黑衣裳戴着黑眼镜,闯进来就把七儿姐姐给抱走了,邵一哥哥没办法,只好跟着一起坐进车子里……” 他说得绘声绘色,一旁的几个中年汉子也低眉丧眼的。 然而众人口中被强行抱进车里的七儿完全没有同样的情绪,她腿脚不好,除了几个村子鲜少到其他地方去,更别提坐小汽车了,她扭着身子扒着车窗,颇为兴奋地看着窗外的景色飞快的倒退着,那轮快要燃烧起来的红日随着一同前进,而后是村子那条小河,在车上看才发现河水还挺深的。 邵一托着她的身子,让她看得更清楚点。 “两位,虽然我认为以你们的年纪,并不像是有驱邪经验的样子,但既然太太推荐了你们,我自然是必须照办。” 坐在副驾驶的男人带着高傲与优越的语气,抬着下巴,透过后视镜瞧着七儿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模样,十分讽刺地勾起嘴角,说道:“简单的跟你们说一下情况好了……”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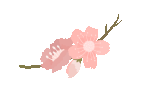
说话的男人姓李,是一位富商的助理,据说还是有点不远不近的亲戚关系,因此总觉得自己比其他的工作人员优越些。 他说这次出事的是富商本人。 其实先前就出现过一些莫名其妙的状况,但是大都是富商周围的人发生的,并没有涉及他本人,所以便没有多花费精力,谁知道前几天不过是去河边村巡视了一趟,回去之后就…… “原来河边村说要拆迁是真的呀?”七儿腿脚残疾,趴窗趴了一会儿就累了,她年纪还小,但是说话却十分的利落流畅,声音清脆,“我还以为就是说说而已呢!” 李助理似乎很不喜欢七儿,大约是瞧不上她是个残疾,说话敷衍至极,“拆是肯定要拆的。” 这么一句话说了就不再纠缠这个话题了,而是继续说明富商的遭遇。 原来富商自从打河边村回去后,第二天左边的腿上就生了一个指头大小的脓包,起初还以为是让什么虫子咬了,去医院也说是毒虫叮咬所致,开了些药膏回来抹。 然而药膏并不起作用,涂了两天反而严重了不少,脓包破了皮,里面流出黑色的粘液,不但腥臭难闻,而且沾到完好的皮肤上立马就是一片黑色点点,那些点点短时间里就会长到豌豆大小。
|


 主页 > 另类小说 >
主页 > 另类小说 > 


